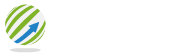我们的邹升华老师
赵若果
我们的初中英语老师邹升华,告别人生舞台快有十个年头了,我们经常提起他。提起他,我们的心情都很复杂,他是一位好师长,也是一位失败的英雄。
1
他是我们黑池镇南社村人,从小就很好学。知识青年下乡那会,他初中没念几天,就回乡接受锻炼了。当时他人小,个头也不高,可是干起活来,舍得出力气,所以和那些壮劳力一样,一天照样能够记个10分工。那几年,他迎着日头起,伴着月亮眠,稍有空闲,便四处找书来看,日子倒也充实快乐。
1972年,尼克松访华,紧接着中日建交,广播电台随之开播外语讲座节目。村里的高音喇叭,突然响起咕哩呱啦的外语教学声,搞得大家莫名其妙,可是他的心弦,一下子被拨动了。他瞪大眼睛,伸直耳朵,听了几次,便向父母要了钱,抽空跑到县城去,给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,给自己买了一套英语听讲用书。
自此之后,他一刻钟都不愿意耽搁,先预习,再听讲,后复习,把所有的时间充分利用。夜里点灯熬油自不必说,有时候,白天下地干活,还要把宝贝收音机背在身后,一旦休息下来,就蹲在地头,贴在耳朵上。社员们感觉他古里古怪,“泥腿子,学外文?”猜想他一定是中邪了,私下里叽叽喳喳,免不了一番讥笑叹息。可是那些有点见识的人,却认定他是一个有志青年,心下都给他竖起了多年不曾给人使用过的大拇指。
1973年,邓小平复出,高中复课三届联招,他的人生迎来了真正的转机。听说县里派来了一位英语老师,他兴奋得不得了,和同学一起,拉起架子车,蹦蹦跳跳,从街头车站接了回来。
接来的老师很年轻,高个头,很洋气,听到说老师此前在北京学习生活过七年,他羡慕得大喊大叫;急切请教几个问题,老师口语流利,发音纯正,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,心想,“老牌大学生,还真不是吃干饭的。”
要知道,这次他们接到的,正是1969年毕业、留校三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高才生,后来扎根我们黑池高中,捂热一片贫瘠乡土,也让自己声名远播的李瑞礼老师。
他如饥似渴,不住地念叨“得遇良师,人生大幸”,暗地里没少给自己“添码加力”。他一有机会,就跑到李老师办公室,把遇到的问题,随时请教。不料,两年的高中生活很快结束,他又不得不回到村里去。
不过,他并不消沉气馁。两年多时间里,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幻, 他也从没丧失过对希望与追求。他一边照样出工,参加集体劳动,一边继续拿起书本,收听英语讲座。好在家离学校近,可以随时向李老师请教,他也有了扎实基础,自学起来相对轻松多了。
1977年,恢复高考,他两次应考。第一次,为了等待录取通知书,他真的是备受煎熬。那些日子里,他茶饭不思、坐卧不宁,他伫立家门、引领而望,明明感觉应该来到,却终究不见来到。为此,他一度沮丧,消沉,彻夜难眠。严酷的现实提醒他及时抖落灰尘,重新振作,继续应战。这一次,成绩已经超线了,可是在体检的时候,却得到通知说,“很遗憾,你是个罗圈腿,并不符合录取条件”。他一肚子委屈,躲开父母妻子,痛痛快快大哭了一场。
在人生的这个重大关头,他的遭遇是不幸的。但是,他的不幸,却成全了我们的快乐。
那几年,村级学习实行七年制,英语教师极度缺乏。他便以民办教师的身份,来到黑池社中,做起了我们的、也就是那年公社集中招收的两个初中班的英语教师。
2
他给自己改了新的名字,邹升华。寓意很明确,他要以自助、自强的名义,追求人生的“升华”再造。
他激情饱满,活力四射,顿时给简陋的校园增添了鲜活的气息——当时他因为等录取通知书,晚到了一个月。一时间,我们真的搞不明白,究竟是英语课程赋予了他独特的魅力,还是他的个人魅力,赋予了英语课程独特的风味。总之,他的精神气质和行事风格,都与他的外语教师身份高度协调,同学们非常喜欢他。凡是与他有关的信息,大家无不津津乐道。不论是当面称呼、还是背后说起“邹老师”这三个字的时候,那腔调、那口吻,饱含着说不尽的敬慕与赞美。更何况,他还有一个了不起的标签,自学成才!
他的特点非常鲜明。个头不高,身材比例其实也不协调。皮肤是光滑白皙的,脸盘也是饱满英俊的,只是前额突出,鼻梁隆起,颅骨长大异乎常人。好在他会打扮,浓密的乌发,被剪成一个大平板;头发根根直立,还要从开阔的额头上斜冲上去,让他显得更像一位精力饱满的斗士。他脚蹬运动鞋,身着运动衣,步子迈得已经够开够大了,身子似乎还不满意,特意前倾,以便加快速度。所以他走起路来,简直像飞,又好像是在蹦在跳。
他三步并做两步,跃上我们教室门前的高台阶,然后疾走两步,大跨步登上讲台,不等同学们道谢完毕,便把手里的课本教案扔在讲桌上,用浑厚的男低音道:
“Class?begin!——上节课,我们学的是什么?我看看,是谁没有下功夫。”
随后,便是一阵东瞅西看。大家心神紧张的要命,却也跃跃欲试。
他问:“It's,怎么读,也读It is吗?”
同学们拿不定主意,有人高声喊道:“是的,也读 It is 。”
他追问道:“对不对?大家说,他的这种说法,Right or wrong?”
这回同学们就吃不准了,很没底气,齐声道:“Right——”
于是他说:“你们看,看,城隍爷庙,正对着戏楼呢!”
说话的同时,还要把头向右压,两只眼睛直瞅自己的食指,仿佛那边真的就有一座戏楼,正好对着一座城隍庙。
他这么一说,同学们就明白了,因为他经常用这种方式,强调自己的否定意见。尽管那时候,对于城隍庙和戏楼,我们的认识都很模糊。
早自习时,他常常比我们先到教室,然后从前到后,从后到前,在过道里不住地转,为的是督导大家张口大声念。有同学发音时皱起眉头拖曳脖子,他会及时模仿,惹得大家一阵开怀大笑。有女生坐姿不正,他也会直接指出,也不管人家女孩子受得了受不了。
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“要学好英语,就得张开口,张开口!要大胆地念,大声地说!”对此,同学们固然都很认同,可是实际行动起来,却不免要把英语当作物理、化学或者生物课,只求记住公式、学会做题,或者说只求会写、会认、会造句子,最终能够应对考试就行了。这种四平八稳、暮气沉沉的做派,以及在他看来,完全是无知、糊涂的认识,包括我们开口说英语时的羞羞答答、畏畏缩缩,都令他非常恼火。他经常厉声传授机宜,“我不管你们怎么看待我的英语课,我只要求你们念,你们说!到时候,你们就会明白,只要会念,就能把单词写出来。知道吗,记单词,有的是窍门!”
因此,课堂上,他不但要组织大家开展情景对话,还会轮番叫人站起来读课文,背单词,念句子。可是大家懵里懵懂,个个舌根发硬,磕磕绊绊念下来,怎么听都土里土气,不对味道。他完全相信朽木不折,金石可镂,所以,恨不得马上就在每个人心里燃起一把火。他劲头十足,还把音标、语法这些课本里暂时没有的内容,也要一点一点添加进来,传授给我们。课堂时间不够用,便把自习用起来,自习时间也不够用,便把课余时间挤出来,课余时间还不够用,后来干脆把星期天也占它半天。初二暑假,他就给我们系统讲授过《张道真英语语法》最初几章。当然了,不收任何费用。
也就是在那个充实迷人的英语之夏,在同学们中间,传阅过他的那本《张道真英语语法》。拿到手后,我如获至宝,小心翼翼,集中精力兴奋阅读,把前部几章的要点,一概抄录。记得那时候,为了写好英语书法,我还给自己弄到了一支秃头蘸笔。唰唰唰,书写完一行,便像模像样地把笔插在墨水瓶上,让它休息那么几秒钟,为的是品味那种潇洒劲儿。他看见了,侧起头,瞅着我哈哈一笑,“也想当老师?”然后抚摸一下我的头,“嗯,书法还行。”
为了鼓励大家练习口语,有一阵子,他还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门外陆续守候,准备与他当面对话。所以,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,经常就有同学忽然从校园东边的篮球场上冲出来,一边衬衫抹汗,一边飞过人群。不用说,那是预备“觐见”去了。也经常会有过不了关的同学,端起课本,缩着身子,守候在他的办公室门外。表面上看,个个满脸苦楚,其实心里头,也美滋滋着呢。因此,在我们的几位代课老师中,他的办公室门槛,可以说是差点就被踏破了。从早到晚,都有同学进出的影子。
当时我们那个年级,也就只有两个班。他经常在一班夸二班的学生好,某某门门功课好,学习英语最用功,反过头来又在二班夸赞一班的学风好,某个同学,肯用功,能吃苦,一天的学习任务不完成,就绝不休息睡觉。自然了,这么一来,同学们之间、两个班级之间,那种比学赶帮的气氛,就更加火热起来了。
他经常宣传我们说:“皇天不负有心人。你们赶上了好时候,现在外语人才,极度缺乏,只要考上北大、清华、北外、北二外,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。你们也很幸运!只要能升入高中,就能做李瑞礼老师的学生。我不相信,其它地方,还有比这更好的条件!” 说得我们无限向往,心里自然是摩拳擦掌,一路小跑起来了。
我们班上有一位女同学,学习成绩很好, 家里忽然发生变故,几次想退学回家。他一再劝勉,引导她、帮助她卸下包袱,安心上进。后来考上了很不错的大学。
他对酷爱英语的学生,更是设法鼓励,恩遇有加。那时候,陕西广播电台每晚十点多,有一个英语教学节目,他不但每天必听,而且还找来几个同学和他一起听,一起学。私下里和老师相聚,那感觉自然与课堂上大不相同:校园里一片静寂,我们一起围坐在他的周围,守着他的那台红色收音机,接受额外的知识滋润,那种快意的心情,自然饱含了得受恩宠的庆幸与感激。哎,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呀!他与我们推心置腹,平等交流,语气间,既像是父亲对子女的叮嘱,也像是大哥对小弟们的期盼与关爱。印象最深的是这么几句:“师傅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。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“除了搞好学习,其它事情,你们一概不要让它进脑子!”那催促上进的心情,好像是恨不得揠苗助长。可惜我们这个学习小组,后来只有酷爱英语的张宪鼎坚持了下来。
为此,张宪鼎加班加点赶进度,他也就精心辅导,有时学到兴头上,便命令宪鼎不要动,自己则跑去教师灶上打来饭,两个人一起吃。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恩典。那时候,同学们、不论男女,一天三顿,都只能享用周末从家里背来的馍馍、红苕,外加每顿学生大灶上免费供应的一碗稀饭,所谓菜品,无非是油泼辣子、盐拌辣椒面、或者一瓶到了后半周就要泛黄变味的大葱炒青椒,因此,肠胃时常冒酸水、闹别扭。当然了,张宪鼎也真做到了不辱师德,后来居然连跳两级,在李瑞礼老师的栽培下,高分考入北京外贸学院,成为人们一度热议、羡慕的对象。
3
初中三年,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,也就只有两年。但是,他留给我们的故事,却丰富多彩,至今想来,仿佛就在昨天。
他酷爱运动,打起乒乓球来,反手扣杀,正手拉送,那真是挥洒自如,游刃有余。一有空闲,他就会邀同学在我们教室门前的水泥案子上打几局。要是有谁能和他势均力敌,对打一场球,那会让人自豪羡慕好几天呢。所以,在他的身边,也经常活跃着一群喜好运动的同学。
我们非常喜欢英语课。每次上课铃声一响,总会有几个同学,拥肩搭背,抓住教室门框,侧身探脑。非要瞅见他的身影,这才立即缩身,纷纷溜回座位,同时喊,“赶快唱,赶快唱,邹老师来了!”于是大家立即肃静归位,挺直腰杆,“A B C D E F G——” 咿咿呀呀,唱起《字母歌》来。
我们还组织过一场英语晚会。时间是初二那年的秋天。在刚进二道门的三间大窑洞前,早早挂起电灯炮来,得到消息的乡邻群众,也早早赶来,与同学们一起,在窑洞前空地上围成一大圈,等候看热闹。其中的一个英语短剧是《半夜鸡叫》。一班的刘竞林高个头,擅长演技,口语也不错,所以就扮演周扒皮,张宪鼎短小结实,口齿清晰,扮演高玉宝。我们二班的一帮同学,则各披了一块从老乡家借来的包棉花用的白色大方布,趴在地上,颤着音,“ 咩咩~咩咩~”,只顾乱叫。
哄堂大笑中,刘竞林戴个黑色礼帽,手拄文明棍,缩着身子,轻迈大步上场。就这么东瞅西看,鬼鬼祟祟在场子里转了一圈,然后去了鸡窝那边,用拐棍向里捅了几下。
“Cluck,Cluck,Cluck——”有人就扮演鸡叫。
刘竞林开始清理嗓子,故作镇静地耸肩拱腰。不料,长工打扮的张宪鼎等几个同学早已悄悄上场,从后边揪住了他:“What are you doing?”
刘竞林缩起脖子,干叫道:“I am the boss.”
几个人齐声道:“Hige, What are you doing?”
刘竞林扯拽脖子,学鸡叫:“Cluck,Cluck——”
那边鸡叫得更欢了。
刘竞林扭过身子,一副东家嘴脸:“Now stop!listen to me carefully. All of you, must get up, when the cock is crowing. Or you can't get the money from me. Are you clear?”
张宪鼎高声道:“Yes. Money, money, we need money.”
刘竞林趾高气扬:“I have many many money!I have more money than the stars!”
张宪鼎故意苦腔道:“Look at my host, it's still early. Look at my host, it's still early.”
刘竞林瞪眼叫道:“ Get up!Get up!The cock has crowed.”
张宪鼎挺身向前,高声道:“It's still early. It's just getting dark.”
刘竞林举起拐棍要打人,不料羊群受到惊吓,满场子乱跑起来。
刘竞林打不着高玉宝,只好把拐棍在空中乱舞,然后又转过身来,挺着肚皮道:“I have a lot of sheep. I have so many many money!I have a lot of sheep. I will have a lot of money!”
老实说,演员的对白,我们并不全能听懂,但照样意趣盎然,笑声不断。
还有一个节目,我们二班的王和平,红头绳扎着个朝天小辫,背着小书包,蹦蹦跳跳出场,飞快地场子里跑了一圈,表示自己正在回家的路上。然后是一番动作,开口道:“ Mother、Father真快乐,I 在学校读book,各门功课都good,只有English 不及格。”惹得女生不住地捂嘴,男生不住地捧腹,满场都是笑声和淘气鬼的尖叫声。
当然了,这天晚上,也让同学们各自得到了几句顺口溜。比如,“I have many many money!”就被大家挂在嘴边,持续取笑打闹逗乐。
4
他走的很突然。春节过后,回到学校,我们才得到消息说,邹老师不教我们英语了,他去进修了。大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,同时也仿佛舒了一口气,心想,再也没有人逼迫我们学习了。
进修期间,他曾经回过一次学校。得到消息后,我们跑去看他。他则脸色铁青,呼呼喘着粗气。我们大惑不解,又不敢出声,就这么面面相觑,偷偷交换了一阵眼色。忽然,他站起来,咬牙切齿地道:“你们知道,我为啥没考上大学吗?” 那说话的神情,显然已经不把我们当学生看了。我们很不适应,却也马上反应了过来。他继续道:“你们知道吗,居然有人敢冒名顶替!”我们大惊失色,连忙问, 究竟是怎么回事?他继续怒火中烧,并不准备告知原委,只是继续对着天空大发牢骚,对着空气述说自己的怨恨。我们真的、真的替他难过,可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,心脏就感觉被人一阵揪扯,深刻地意识到,我们心目中的英雄,我们最可敬爱的邹老师,原来也会诉求无门,弱小无助。
从此之后,我再也没见到过他,只是非常留意他的消息。他从渭南师范进修结业之后,转了正,开始担任高中教学工作。在路井中学工作期间,喜欢把我们黑池初中的学生当作样板,鼓励自己的新学生刻苦攻读,扎实求进。路井与黑池两个乡镇,直线距离其实不远,只是隔了一个令人胆寒的金水沟,所以多少年来,两地群众很少互通有无。他每周回家,必然要从这个人迹稀少的“景阳冈”上,一下一上花上两个多小时。有那么几次,他就带着两个男同学,陪伴他回家。
他一向不甘寂寞,一直琢磨着如何走出新天地。后来他还在县政府某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。在那里,他发现,自己的率真、求实,实在是极不相宜,人家喜欢的曲意逢迎,相互酬和,拍拍打打,也让他慢慢感觉到别扭、错位。这期间,就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1992年的某一天,他正在县城某路口守候公交车,突然有一中年男子,骑着一辆破自行车,直冲过来,他躲避不及,被撞飞到几米开外,顿时颅骨开裂,血流如注,失去了知觉。慌忙转院到西安抢救,五十多天一直昏迷不醒!
事后,作为赔偿,肇事者只拿出了一百五十块。因为此人“穷得叮当作响,家里只有几间茅草房。”他苦笑一声,只得自认倒霉,知道深究也没什么用。又听我们的师娘诉苦说,那家伙当初离开医院要回家,没路费,“我看着,又气又别扭,就给了点盘缠。”他愉快地听着,继续苦笑一声,只感激自己逃离了鬼门关。并没意识到,由于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的输血不严格,结果血源污染,丙肝病毒已经在自己体内潜伏了起来。
住院欠了不少钱,家里顿感拮据紧张。他高叫一声,“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!”便踩着时代浪潮,下海经商了。他亲自押着大货车星夜南下,准备与他自己的渭南同学南北联手,在深圳做家乡的苹果销售代理商。
不料,货到街头死 ,他遭到了当时常有的那种地头蛇最铁面无私的打压。结果算下来,连路费也赔了进去。他不服输,还是在我们同学张宪鼎的帮衬下,他租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小铺面,从此坐店零售家乡特产,师娘及孩子都接了过去。
生意很快步入了正轨,他还得有空暇,受邀到一所民办学校去,代了一年多的英语课。生意越做越大,人手开始出现短缺。于是,新的不幸接连发生,他居然三次被骗,而且次次都是因为自己的古道热肠!一次,一位可怜兮兮的年轻小伙子,跑来说,自己是陕西的,眼下生计无门,想讨个工作做。他立即表示出自己的十二分的同情,并马上予以周济接待,安排到自己的店里,照顾生意。结果是干了不到一个月,店里的东西全被卷空,不见了人影。他得到消息后,暴跳如雷,羞愧难当。他瞪大眼睛宣誓说,“从此,我要把良心挖出来喂狗!我要铁面无情,做一个真正的活阎王!” 可是,正如人们常说的,次次都上当,当当不一样。就这么着,他摇头晃脑,深深地叹息,终于承认自己已经不会做人了。
后来,渭南果业协会关门歇业,苹果货源断了线。又试着做了一阵子米面粮油生意,发现很难入道,于是一家人变卖了刚在深圳购置的一处小房产,不无失落地回到了家乡。
到家后不几天,就有人登门,聘请他去做英语教师。于是,他去了华县。那时候,他的老师、同时也是我们的老师、德高望重的李瑞礼,已经做了咸林中学校长。他们偶尔会见面。据李老师回忆说,“交通事故,明显有点后遗症。他好像也不太愿意提起过去的事情。”
再后来,他去了山西,也是一家民办学校。在他的努力下,学生的成绩大有提高,于是家长高兴,校方认可。几年时间里,他多次受到嘉奖鼓励。但是,校方对一位教师的处理,出现了不公,他出面主张,与校长大吵起来。为此他要辞职,校长慌了手脚,几位家长也闻讯赶来,陈请留任,可是他去意已决,随之去了万荣县。
在万荣干了不到一年,他就开始感到疲倦乏力,呕吐恶心、低烧不退。以为是感冒,就近治疗了好长时间,还是不见好转,只得辞掉工作,回到了家里。到县医院复查,病因终于找到了,居然是丙肝!而且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肝腹水。于是他被隐瞒了起来,有朋友经常上门,陪他聊天, 提起山西往事,抱怨他爱管闲事。他正色道:“我,路见不平,就要拔刀相助。” 然后是低头无语。令人揪心的是,他脸色铁青,孤身独坐,全身笼罩着浓厚的抑郁气息。也许,他已经明白地意识到,当今之下,金钱成了唯一的尺度,自己的所谓义举豪言,其实是很苍白、很乏力的。
我们的师母,一位真正的贤妻良母,多少年里,一直在家务农,侍奉高堂,精心养育一双儿女,帮他分担后顾之忧。据师母说,他也有点抑郁症,病根其实很久了,别人发现不了,他一直在偷偷控制。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,他时而发誓要东山再起,时而意志消沉,茶饭不思,发起脾气来,谁也不敢说什么。他经常气喘吁吁,大汗淋漓,重拳击案,高声叹息。
得到他去世的消息,我们无不哀伤怅惘,心中涌起的,是一股壮志难酬、英雄末路的悲凉与凄怆。
同学们纷纷从各地赶回,专程为他送行。我们二班的老班长王宏海谨致挽词,表达同学们的哀思:
一九七八,高考初复,
英语师资,城乡匮乏。
同辈学子,畏外如虎,
倾力攻之,收效平平。
既挫总分,且扰余科。
黑池同学,幸逢邹李,
一脉相承,心血浇培。
英语短剧,风华正茂。
师生相辉,傲立潮头。
拉升各科,四方震动。
汗撒金水,惠泽秦晋。
先生升华,荣罩百里,
桃李天下,师恩永存。
我们都同意说,在高考这个人生重要竞技场里,对于许多农村、甚至城市中学来说,外语无疑是一只最需要严肃对待的拦路虎。1983年,来自我们黑池社中两个班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,都顺利步入了大学的门槛。其中,王发运、赵建民两人中榜北京大学,李宏茂中榜清华大学,而王发运还荣膺当年省文科类、外语类的双科状元。一个偏避乡村的普通中学,一群视野狭窄的农家孩子,能够赢得这个好的成绩,自然会引起轰动,自然会引起广泛的热议。所以,在渭南地区、甚至在陕西基础教育界,就有过一个所谓的黑池中学83级现象。这一现象的产生,就英语单科而言,固然得益于学养深厚的李瑞礼老师的巨大付出,但同时也得益于我们的邹老师,以及他的继任者,他的黑池高中73级同学,温和有趣的翟文选老师早年一起给我们储备的厚重知识积淀。也就是说,是他们师生三人的并力苦耕,奇迹才得以顺利产生。
只是,我们也同时遗憾的联想到,他,我们敬爱的邹老师,原本也可以像李瑞礼老师那样,扎根一方乡土,泽被更广泛人群的。可惜,唉,他却以自己英年早逝的冷酷方式,向社会乱象发布了一次最严厉的控诉。
好在我们、以及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,一团火熄灭了,一颗高洁的灵魂得到了永恒的自由。
【作者简介】赵若果,本名赵新民,陕西合阳黑池人,陕师大中文系毕业,曾在西北农业大学任教,后多年从事新闻工作。
作者近期作品展示
赵若果 || 老师业文
赵若果 || 恩师佛进
金水文学 感恩有你 感谢您的赞赏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