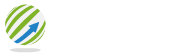荞麦饼的味道
作者简介:龙杲,平江人。农民。
五十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,那年我五岁,父亲在一座叫驻牛尖的山上烧炭。
天下着蒙蒙细雨,父亲一大早就进山了,大概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,父亲还没有回来。家里已经断粮了,父亲进山的时候,除了肩上扛着扁担,手上提着柴刀,并没有带上中饭或者其它可以用来充饥的干粮。母亲到邻居家里借来了一升荞麦,就着大门角落里的石磨磨荞麦,一边推磨一边咿咿哦哦哼着一曲至今令我牵肠挂肚的童谣,逗着摇箩里的弟弟。
荞麦粉磨好了。母亲先是加水调成糊糊,再做成一个个的荞麦饼,在大锅里蒸熟。揭开锅盖的那一刻,看着一个个呈现着淡紫色的荞麦饼,闻着随蒸汽四散开来的荞麦特有的香味,在那个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,用乡亲们的话说是,只要看到能吃的东西,都能使人的喉咙里伸出一只手来,何况是香喷喷的荞麦饼。母亲把荞麦饼装到一个大碗里,让我趁热吃了一个,并竖起指头说,只能吃一个,我听话地点了点头。母亲也吃了一个。但她只是在口中嚼了一下,便嘴对嘴喂起了早就在一旁嗷嗷待哺的弟弟。
母亲把几个荞麦饼放进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挎包里,然后对我说,你背着荞麦饼到驻牛尖的山脚下去等父亲回来,父亲早上出门就喝了一碗稀饭,怕顶不住。
我背着装有荞麦饼的挎包,走过人烟密集的彭家大屋,沿着一条清代嘉庆年间修凿的傍山灌渠,来到了驻牛尖的山脚下。这里是村庄与大山的临界点。一眼望去,山脚下是一条乱石嶙峋的小溪,隔着小溪,一条羊肠小道从对面的半山腰挂下来,半山腰以上云遮雾罩,蒙蒙细雨洒在山脚下的树林里,又从树叶上聚而成珠掉下来,发出嘀嘀嗒嗒的响声。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,母亲的意思,也就是叫我在这里等候父亲归来。我当时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完全忘记了母亲的叮嘱,我没有丝毫犹豫,背着装有荞麦饼的挎包径直跨过那条小溪,沿着羊肠小道一步一步地向云雾深处爬去。
越往上山路越陡峭,雨丝更绵密,雾更浓,听得到深涧中哗哗的流水声和小鸟啁啾的叫声,却分不清几十步开外哪是山哪是路。也不知走了多久,直到前路传来父亲咳嗽的声音,看着戴着一顶泛白的黄军帽,脚上穿着草鞋的父亲在浓雾中越走越近,身影越来越清晰,不知为什么我的泪水一下涌出了眼眶。父亲惊愕地看着呆呆地站在路边的我,连忙放下肩上的柴担,蹲下来抹去我头上的雨珠和脸上的泪珠,然后紧紧拥抱着我。那一刻,我看到父亲的腰上,紧紧地扎着一根我叫不出名的野藤,像是当年他精神抖擞地扎着武装带,走下抗美援朝的战场一样。
我知道父亲一定饿了。我取下挎包,塞到父亲怀里。父亲接过挎包,翻开盖子,并没有急着把荞麦饼拿出来吃,于是把头埋在挎包里面,深吸了一口气,口中说道,真香。我也知道真香。来的路上我总是一边走,一边把挎包拉到胸前,举到鼻子底下,闻着荞麦饼那沁人心脾令我垂涎欲滴的香味。父亲拿出一个荞麦饼,塞到我手里,我推过去说我吃过了,妈妈说的只能吃一个。父亲说现在妈妈不在,吃了她也不知道。吃过了还能吃,不是说“过条坑,吃碗粥”吗。荞麦饼的诱惑对我实在太大,经不住父亲的几声劝,我接过荞麦饼坐在路边的石头上,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一会儿,父亲也吃完了剩下的两个或三个荞麦饼。父亲站起来伸了伸腰,紧了紧腰上的野藤,又抬头看了看天色,说,我们回家吧。说完父亲挑着柴担,我背着已经空瘪的挎包,一前一后地走下山来。
当初不知道“过条坑,吃碗粥”的含义。长大的我才明白,这是乡里的一句俗话,意思是即算吃饱了,如果过了翻过一道坑的时间或者距离,人就可能感到饥饿,也就能吃一碗粥了。可父亲在山上伐树烧炭,一天下来,不知要翻过多少的沟沟坑坑,不知多少次在低矮的炭窑里爬进爬出,早就饿得勒紧了腰腹,这小小的几个荞麦饼,又怎么够他自己塞牙缝。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,父母正是用无私的大爱,节衣缩食呵护着我们兄弟长大。
如今村里已没有人种荞麦了。今年清明节,我在镇上的超市里,买了两斤荞麦粉,学着母亲一样调粉,做了一张大饼,蒸熟后摆在父母的坟前。荞麦饼的香味和着檀香的香味在那个春暖花开的清明随风飘远。
图片:网络